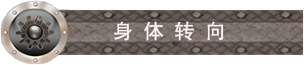
身体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它是由自然、社会与文化构成的,另一方面,它又是构成世界的原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各种人文学科都开始急剧地转向于探讨社会生活中的身体,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的生活世界。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人口处镌刻有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认识你自己。”这正是西方思想史包括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努力所向,即要想真正认识你自己,反思自身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对身体的观照有助于澄清笼罩在身体之上的暧昧想象,有助于重建明晰的身体意象,有助于挖掘人的潜在本质,当然,也有助于追寻西方社会学对人的理解之路。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的存在与身体息息相关。无论灵魂多么高贵,身体的寂灭必然导致灵魂的消散,从而取消人的现实存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有一个显见和突出的现象:他们有身体并且他们是身体”①。也正因为如此,对身体的探讨本质上就成了对人本身的探讨,身体的命运实际上也正是人自身命运的一种生动写照。在西方思想史上,依然遗留着各种有关身体论述的踪迹。 一、西方思想史上的身体踪迹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被具体表述为身心二元论。在古希腊语境中,身体代表感性,心灵代表理性,从认识论上来说,感性产生的是意见,理性导致的才是真理。古希腊哲学的最高追求是对真理的发现,以及对意见的弃绝,很显然,真理高于意见,所以,心灵高于身体。可以说,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就是一部心灵压迫身体的历史,而这种压迫主要是通过柏拉图才真正完成的。作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代表,柏拉图的哲学主要建立在实在与现象的二元划分基础之上,他将世界划分为具体的感性世界和抽象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本原,是最本真的实在,它决定了感性事物的存在,感性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分有和摹仿的结果,感性事物正是因为分有和摹仿理念才得以存在,感性事物仅仅是理念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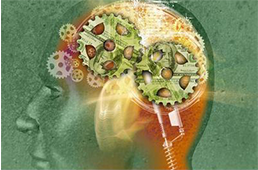
因此,这种感性事物的存在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是非本真的、无意义的。与这种二元论世界观相对应,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中,柏拉图的态度是异常鲜明的,他对于肉体抱持一种强烈的敌意,他对肉体的态度始终是贬抑和否定的,这使得柏拉图的哲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一种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在柏拉图看来,身体是一种虚假的存在,是一种无意义的存在,身体是心灵的牢笼,身体是心灵的坟墓,身体阻碍了心灵对智慧的追求,而哲学家毕生的追求目标就是智慧。智慧本身是一种极其纯净的东西,只有当哲学家真正摆脱身体的羁绊,灵魂才能获得自由,只有自由的灵魂才能达到对智慧的追求。柏拉图的哲学对西方思想影响非常深远,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N.Whitehead)曾毫不夸张地评论到: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不过是对柏拉图哲学所作的一连串脚注。不过,柏拉图的思想对于身体发展来说呵能就是灾难性的了,从此之后,西方社会就开始了漫长的身体压抑和污名化时期。直至文艺复兴时期,虽然身体逐渐走出了神学的禁锢,但是,它并没有获得长久的哲学注视。通往知识之路的是意识、心灵和推算的内心世界,身体在知识的通途中依然没有找到它的紧要位置。即使在作为柏拉图理论的最理想传人的近代哲学家笛卡儿那里,心灵同身体仍然是分属于两个不同区域,对此,笛卡儿最经典的表述就是他那句标志性的经典名言:“我思故我在。”不过,“我思”所指涉的自我不是身体自我,而是精神自我、是我的灵魂。换句话说,笛卡儿认为,正是因为有了灵魂,所以才有了我的存在。我是灵魂性存在,而不是身体性存在。在笛卡儿的思想中,精神和身体是完全不同的,“在身体的概念里不包含任何属于精神的东西;反过来,在精神性的概念里边也不包含任何属于肉体的东西”①。在柏拉图那里,身体是被贬抑的,但是,通过身体的感性训练,灵魂还可以“回忆”起理念世界中的印象。而在笛卡儿这里,身体不仅被贬抑,而且,身体和心灵是根本不相关的两种存在。因此,布赖恩·特纳(B.S.Turner)曾就此评论道:“社会科学普遍接受了笛卡儿的遗产,在笛卡儿这里,身体和心灵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的二元论相信,在身体和心灵之间没有互动,因此,这两个领域或者主体都是被各个不同的学科分别提出来的。身体成为包括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主体,而心灵则成为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的主题,后来,这种分割成了社会科学基础的一个重要特征。


芭芭拉·杜登(Barbara Duden)声称,人口统计学使一定历史与文化中的身体失语,将其简化为现代固定的形象。圆中国人口史所描述的历史行动者似乎与我们有着在本质上相同的身体,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对其身体的运作方式更加无知。∞前文对功效、选择和动机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原因一结果和现代科学所公认的身体形象做出的。但是有必要超越这一视角,审视中国人种生物学对生育的理解,即对身体和婴孩如何被带到这个世界上——“如何”及“为什么”控制生育的“当地人的”理解。我应该强调的是,这里我们所讨论的不是一个孤立的“中国人的”身体问题,而是一揽子不同类的问题。现象学的身体(有血有肉、有骨骼和筋腱、有心肺等器官、有神经和官能的肉体——也许与非物质性的心理、灵魂或精神相协调的,也许截然不同的身体——通过它我们存在着,也认识到我们自己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在不同社会中的建构和组成是有差异的,即使在同一社会里,身体也是由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经历着。@98杜登的研究揭示出,18世纪德国地方市镇中的普通人所具有的生物学观念与我们有极大的差异,而且其生理上的经历和期盼相当令人惊异。这里仅观察~种身体功能,如月经,今天我们只将其与女性的生育联系在一起国:对于杜登的国民而言,月经不是与生育相联系,而是被视为健康的必要因素,因为它可以冷却或净化身体;如果出现闭经,人们更可能考虑钧是这有害于患者的健康,而非生育问题;如果月经不能恢复,相类的血液溢出将减轻其恐惧,诸如流鼻血、伤口化脓;尽管男人的身体建构不需要这些规则的血液溢出,但月经并不总限于女人,也并不限于哺乳期;另外,如果妇女的月经延续至老年,人们也不会感到吃惊,当然其长寿的原因将被归结于此。相比较而言,中华帝国后期医学所讨论的身体似乎更常见、更有预见性,也更“真实”:只有育龄妇女才会行经,男人的流鼻血不会起到与月经相同的作用。但必须当心,不要让二者广泛的相似性使我们看不到其真实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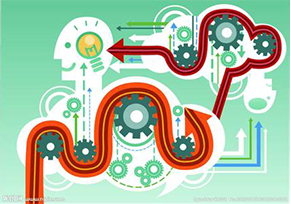
杜登的研究并非专门关于其德国市镇中的人们如何理解生育的,但她的发现许多涉及到艾森纳赫(Eisenach)的妇女和医师如何理解女性的身体,从医师及其主顾如何在高深的理论和民间信仰之间达成相互通融的,这些都是尝试重建艾森纳赫人的生育文化所不可缺少的内容,包括重建其对生产和生育孩子的信仰及其那个社会中不同人的生育策略。
这引发我思考,在中国,人们是如何经历其身体的。南希·斯科普一哈夫斯(Nancy Scheper--Hughes)和玛格芮特·洛克(Margaret Lock)在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里,具体表述了最近大量医学人类学和医学史中所采取的理论立场,其认为从社会和政治维度的抽象中,不可能理解物质性的身体及其表达。o现代科学思想依靠抽象的过程;它向我们呈现出在空间、时间与社会身份上显然都不稳定的“客观的”身体。回有判断力的学者的任务则是要去重建这个表面上与价值无涉的认识论中所固有的价值,去设想科学研究对象的主观性。现象学的身体,那有感觉的、活着的身体在每个社会中都是同一的。但它无法与其所包含的两种深层的经历相分离,斯科普一哈夫斯和洛克称其为“社会的身体”和“身体政治”。在《自然象征》中,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说,那是“善于思考的身体”,是隐喻性的社会体现;斯科普一哈夫斯和洛克辩证应用了道格拉斯的方法,分析了作为象征系统(用于竞争性和等级性的社会关系的更广阔的构架)的生物学表达及其经历。@至于“身体政治”,他们提醒我们,个人权力、卫生保健和医学实践都依赖于手段和身份地位,依赖于布迪厄所称的社会与文化资本,也依赖于简单明了的经济多样性。@在中华帝国后期的情况下,医学制造出一套身体形象,影响到人们对身体的思考及如何体验其身体。宗教的、巫术的、宇宙观的信仰也制造出这些身体形象的变种或可选择的对象。并且关于血缘关系、社会关系的观念,以及活人与死人、父母与孩子、个人与家庭关系的性质都产生对病因的崇信,对建构恰当而“自然的”经历与期望的崇信,对身体的起始与终结的崇信。对谁(通常是陌生人和我们不熟悉的人)有权索要我们肉体的崇信。权力是在对身体及其表达的解构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实证主义的科学史家和医学史家关注的是人类理解和控制自然界的力量。后结构主义的科学史家和医学史家关注的是人们彼此之闾施加的权力,关注的是如同自然事实似的控制力的代表,关注的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的选择视角以及他们反抗统治的斗争。后结构主义者尖锐地意识到,“统治的主要机制是通过对身体的不自觉操控来运转的”o,特别是通过思想的操控,通过制造有关身体的观念或“话语”。
业稚出二辛雨确rt'l化南圈E翻^1^白.“‘亡二x瞳{小、¨、土 ;小、.k

当我尝试再现中华帝国后期妇女身体所经历、被讲述、被谈论以及所上演的不同模式时,也试图再现中国人对身体的不同理解。在感怀他们对身体形象的无穷创造力时,我也相信,所有这些创造的形成都来自于人类生命的延续和繁衍的基本物质需求:吃饭与睡觉,疼痛、疾病与死亡,性、分娩与其他任何制造能够转变为人的弱小生命。我发觉自己与当前女权主义理论的不一致之处,其不考虑物质现实在身份塑造中的作用。@当代性别和性批评理论否定适度的生物繁衍取决于相互矛盾的物质基础,即性欲与生殖的分离,近来避孕技术的发展使其成为可能。生物医学诊疗的高科技手段,使得我们可以将身体只看做是由言辞塑造和填充的躯壳。∞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以为其他社会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脱离肉体的。伊莱恩·斯凯瑞(Elaine Scarry)说:“无论何种疼痛,部分地是以极为独特的方式达成的,其通过对语言的抗拒确保这种独特性。”疼痛不仅是身体抗拒语言的经历,而且是不能被忽视的经历。当有关身体的文本告知我们必须怎样做时,话语及其政治根源就在塑造我们对身体的理解上发挥出比现实更突出的作用。正如芭芭拉·杜登所做的,世界上的妇女不能脱离其外在的躯壳而存在,记住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能奢求精确地再现中华帝国后期的身体形象和妇女与男人的感受,但我认为我们确实可以承认,生育的迫切愿望在人们日常意识的塑造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这些未成形的感受渗透进了医学与社会的话语中,影响和指导着他们,但却不能创制或毁灭他们,甚至也不能完全包容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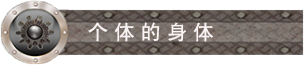
现象学是一种通过“直接的认识”来描述现象,从直接直观和先验本质中提取知识的研究方法。它是对意识哲学的一个批判,是对笛卡儿式的精神一身体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自然一超自然、生理一心理、激情一理性、主观客观等二元对立的批判。对于“个体的身体”的强调主要就是以现象学为理论背景的。作为现象学一个学派的“知觉现象学”,把形而下的身体作为现象学分析的起点,认为人类所有的精神活动都受制于自己的身体特征。因此,只有从身体的角度出发,才可能谈论对世界的感知。这一学派强调身体体验、感知的时空性等,对身心的关系做了反笛卡儿式的思考,即回归“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在”。①受现象学与心理学思潮的影响,一些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关注思维、物质、精神、自我等这些身体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身体是如何体验健康与疾病的,关注身体想象(body image)、身体认知(body perception)等问题。

马克思、涂尔干、莫斯(Mauss)等人的社会学思想,都强调社会化的身体。②涂尔干、莫斯这一学派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身体不仅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是承载着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工具。还有的学者把身体分为生理的身体与社会的身体,强调身体是一种象征系统。③主流的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对于身体、性的研究,都偏向于象征性地来使用身体这个概念,因此“讲述身体和性实际上是在讲述社会的本质”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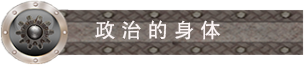
身体政治主要指“对于身体,不管是个体的身体还是集体的身体的管理、监督与控制。它可以发生在生殖与性的领域,也可以发生在工作与休闲的领域,还可以发生在疾病以及其他形式的反常的领域”⑤。身体政治理论与后结构主义思潮紧密相连,并在福柯那里得到了极致的表达。大多数女权主义者也关注身体研究。她们的主要观点是,个人的即是政治的。
体在传统社会科学中的缺席,被部分地归因于男性在这个领域长期占有的主导地位。因此,女权主义者在“体现”(embodiment)与身体的研究领域中不断涌现出新的成果,身体研究中的社会性别视角也开始凸现。比如,法国新女性主义中的一派对于女性的身体进行了重新诠释,一些深受福柯思想影响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者十分强调性的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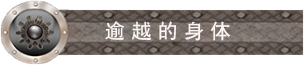
“身体社会学”的创建者特纳,把已有的身体研究放在社会变迁的历史中作了系统的回顾,突出论述了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与商业化、政治上的女权运动以及医学实践对于身体的作用。他特别对身体在社会学中的缺席作了详细的分析,并且提出了他的类型学的分析框架。特纳通常被认为属于“社会的身体”、“宗教的身体”这一学派。他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身体在社会中是如何被形塑的”。但是,他也认为应该打破身体研究中所存在的认识论与存在论、身体本身与表征(话语)之间的二元对立。他的主张是不一定非要坚持身体的生理性或者社会性,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①与特纳的论述不同,洛克和冯珠娣等学者近年来提出的“逾越的身体”更加强调身体本身的多元性。在身体研究中,分别从个体的身体、社会的身体、政治的身体出发的三种思潮,主要是批评古典哲学中的身一心二元论以及身体的被压抑、被忽略的现象。“逾越的身体”这一学派则是主要批评社会科学中那种对于个体一社会、物质一文化、主观一客观的分野。以往的身体研究,或者过于强调身体体验而没有给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留有余地,或者是仅仅把身体作为一个承载社会与文化的工具,却无视身体体验的多样性与偶然性。结果,身体就一直被“理所当然化”,成为一种“规矩的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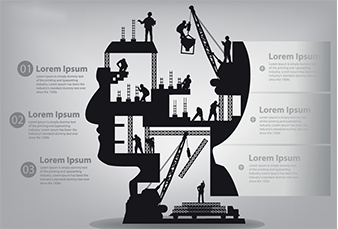
“逾越的身体”这一学派认为,以往的身体研究过于墨守成规,仍然缺乏一种有着历史深度与社会深度的活生生的身体概念(1ived body)。这一学派认为:“可以根据对话语、日常生活、技术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分析来对身体问题进行探讨与分类……这些身体可以同时汇集社会的、政治的、主体的、客体的、话语的、物质的。”②人类学与社会学领域的一些研究,尤其是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的研究,表达的就是这种超越规矩的身体观。布迪厄把身体看做一种资本。他认为,身体的发展通过个体的社会位置、惯习的形成、品位的发展,体现出社会阶级的烙印。③布迪厄提出,身体本身介入了惯习的生产,既受场域的塑造,又反作用于场域。①但是也有些学者认为,布迪厄的理论趋于保守,缺乏对身体的主体能动性的强调,而且对于惯习的形成本身也缺少解释。 一些学者把身体的研究转向日常生活,开辟了对于社会生活的经验性研究的新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认识论与存在论的二元对立,弥补了长期以来身体研究中理论探讨多于实地研究这一缺陷。

比如,有的学者研究了努尔人是怎样感受与经历时间的,这种感受也就是人们对身体和生活经历的感受,而且是暂时的、可变的。②在日常生活研究方面,戈夫曼的“戏剧理论”细致地展现了身体作为互动要素是如何被呈现的。他的最大成就在于“将身体作为行动的要素,使韦伯的理性行动,帕森斯的单位行动重新回到了丰富具体的日常互动——他努力从正面展现互动中个体对身体的控制、监督、运用,探究这种过程与社会规范的相互决定”③。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有一类关于技术与身体的关系、地方性身体(10calbodies)的研究,挑战了社会学和生物学的普遍性假设。“电子人”的概念就是其中之一。它打乱了诸多的二元对立,把科幻小说中描写的、人与机器相混合、肉体与信息相混合、超越了自然一文化等二元对立的那种“电子人”,展现为新千年的一种正常的身体。④还有的学者研究了北美人和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问题,例如,对于器官移植、脑死亡、疾病、月经等的不同感受,也展现了地方性生物学(10cal biologies)的概念。⑤这种对技术性身体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一些激进的后现代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技术的全然否定与不屑一顾。
总之,在这些研究中,身体是体验式的、欲望的、暂时的、地方的、可变的、活生生的,同时又是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物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