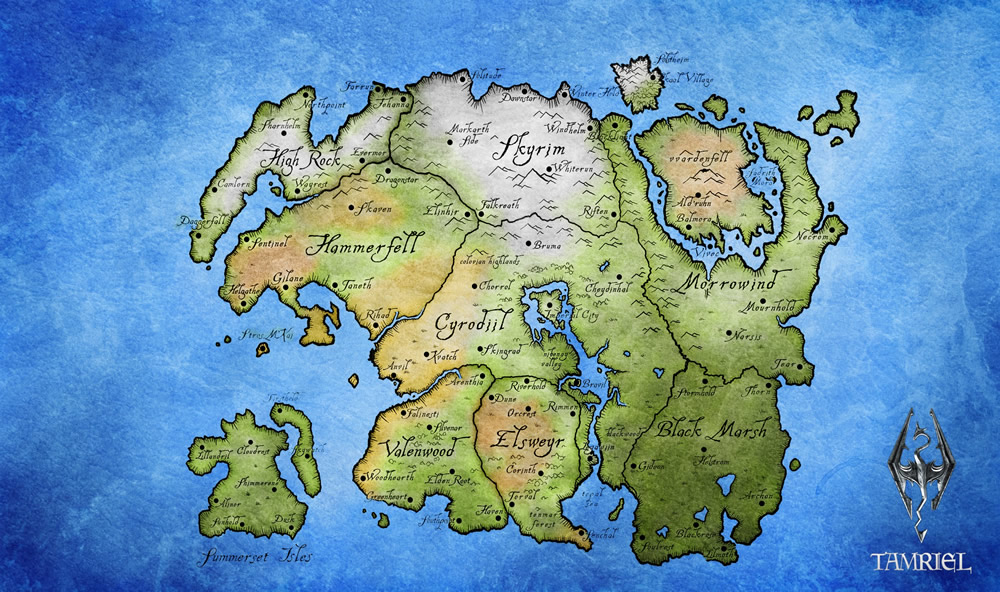儒家和日神的关系
 如果说,与酒神精神相比,道家的弱点在于缺少感性冲动;那么,与日神精神相比,儒家的弱点则在于缺少理性冲动。我们知道,同日神崇拜一样,儒家也不满足于肉体的沉醉,而去追求一种更高的精神寄托,然而这种寄托却无需到抽象的思辨领域和神秘的符号世界中去寻求。儒家不作抽象的形而上的玄思,对于生活现象以外的东西,儒家善于采取一种与其说是聪明毋宁说是机智的态度——存而不论。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的名言,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对于现实生活的执着追求;而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近乎悲剧精神的入世态度,也充分体现了“实践理性精神”的可贵之处。然而遗憾的是,强调理性和实践的结合,这不仅是儒家思想的一大优点,而且是其最大的弱点。正是由于儒家用狭隘的急功近利的态度去看待理性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人理性思辨的能力,束缚了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从而最终导致了科学的落后。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科学的落伍只是近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我们的科学较之其他民族则是遥遥领先的。然而,这种流行的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在古代的西方人眼里,东方的汉、唐帝国是繁荣和强盛的,但是这种繁荣和强盛主要的是由于军事和文化,而并非由于科学。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理论科学,有的只是工艺技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都带有工艺的色彩,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又都带有谋略的痕迹。
如果说,与酒神精神相比,道家的弱点在于缺少感性冲动;那么,与日神精神相比,儒家的弱点则在于缺少理性冲动。我们知道,同日神崇拜一样,儒家也不满足于肉体的沉醉,而去追求一种更高的精神寄托,然而这种寄托却无需到抽象的思辨领域和神秘的符号世界中去寻求。儒家不作抽象的形而上的玄思,对于生活现象以外的东西,儒家善于采取一种与其说是聪明毋宁说是机智的态度——存而不论。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的名言,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对于现实生活的执着追求;而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近乎悲剧精神的入世态度,也充分体现了“实践理性精神”的可贵之处。然而遗憾的是,强调理性和实践的结合,这不仅是儒家思想的一大优点,而且是其最大的弱点。正是由于儒家用狭隘的急功近利的态度去看待理性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人理性思辨的能力,束缚了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从而最终导致了科学的落后。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科学的落伍只是近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我们的科学较之其他民族则是遥遥领先的。然而,这种流行的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在古代的西方人眼里,东方的汉、唐帝国是繁荣和强盛的,但是这种繁荣和强盛主要的是由于军事和文化,而并非由于科学。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理论科学,有的只是工艺技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都带有工艺的色彩,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又都带有谋略的痕迹。
由于它们所使用的思维结构大多不是“因果关系”而是“阴阳关系”,因而与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有着很大的差距。极端的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曾有过很多为中国传统护短的言论,例如论证缠足、纳妾如何合理之类,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却是相当清醒的,他指出:“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方面的,也有纯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字,是无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的确如此,仔细看看:指南针不是电磁学,造纸术不是物理学,传统的火药不是依据化学方程式配制出来的,而活字印刷也用不着电子科学的参与……如此说来,我们长期以来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并非科学,而只是工艺!中国人可以通过反复测算而为圆周率的π值找到一个相当精确的数据,但却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欧几里德式的几何学体系;中国人可以通过反复实践而建造起天坛祈年殿式的精美建筑,但却不可能建构起一个牛顿式的力学体系……。
中国人丝毫也不比他人愚笨,然而理性的翅膀一旦绑上实用的铅砣,就难以高飞远举了。历史竟然如此荒唐,使得每每沉湎于抽象玄思的西方人获得了科学,而念念不忘经世致用的中国却只得到了工艺。在迎接全球性科技挑战的今天,冷静地回顾和总结一下这段历史不是没有意义的。关于这一观点,笔者曾在1986年第6期的《文史哲》上撰文论及,近读1996年8月19日的《报刊文摘》转摘著名科学家吴大猷发表在1996年8月10日《团结报》上的文字,也有相似的看法。“吴大猷说,中国历代的科技发明,如蚕丝、铜器的制造,都早于西方,历史学家一定可以列出很多发明事实,证明中国的科技发展在过去是优于西方的。但是大家陶醉于这些成就的当时,却忽略了这些领先都只是技术而已,中国长久以来就缺乏科学思想的扎根与探求……。吴大猷认为:科学与技术不能混为一谈,过去中国超前西方世界的,其实只是技术。由于对科学与技术的分际认识不清,以致科学思想的扎根工作长期被忽略了,这才是中国长久以来科学发展不及西方的原因。”我完全同意吴先生将理论科学与工艺技术区分开来的做法,只是认为中国科学不及西方的原因要远为复杂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