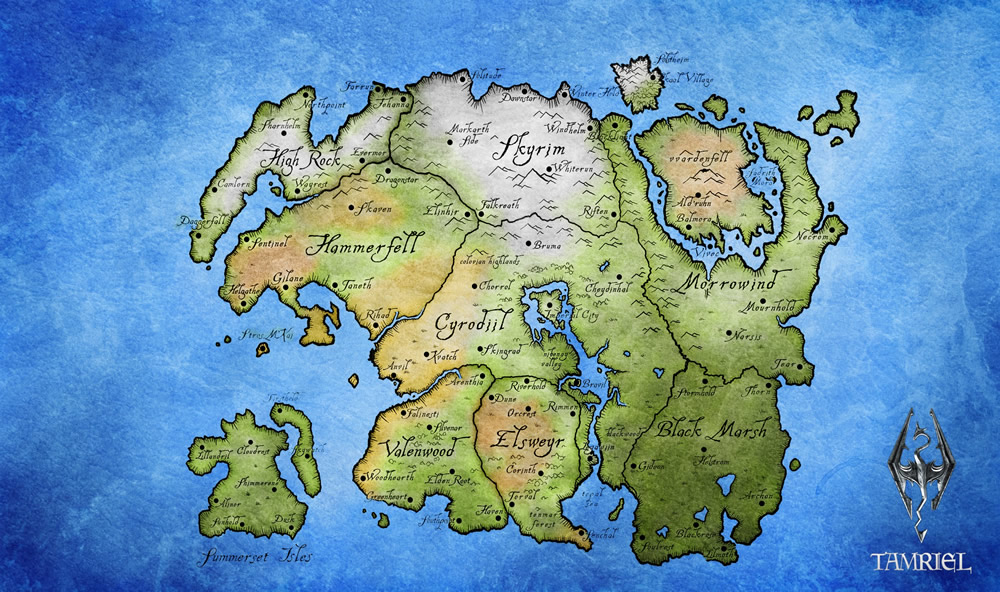如果说,西方体育事业的发达是与狄俄尼索斯式的肉体沉醉有着内在联系的话,那么中国体育精神的薄弱则不得不归咎于老庄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我们知道,与酒神崇拜一样,道家虽然也主张摆脱文明的束缚,恢复原始的人性,有着返朴归真的特点。然而它顶多“绝圣弃智”(《老子十九章》)、贬低理性的作用,却丝毫没有反理性的、本能的冲动;它顶多“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而不会有什么犯上作乱、纵欲妄为的行为。所以,从直接的社会效果来讲,道家思想的破坏性要比酒神精神小得多。然而不幸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深刻的两面性。与酒神精神相比,道家在限制纵欲主义的同时,也就限制了正常欲望的满足;在限制反理性之冲动的同时,也就限制了必要的感性冲动。老子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庄子四十六章》)因而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老子三章》)。“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老子二十八章》)主体的感性冲动衰弱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竟坚持:“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这种拒绝冒险、回避竞争的态度显然与竞技性很强的体育精神是相互排斥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老、庄思想中也有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益寿延年的内容,这些内容通过以后的道教,对于以吐纳导引为特征的气功与武术等中国式的健身方式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致虚静,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老子十六》)便可被视为气功中“意守丹田”的思想根源。又如,“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息之以踵,众人吸之以喉。”(《庄子大宗师》)则可被视为健身中“吐纳导引”的早期实践。但是,这种强身健体之术与严格意义上的体育是有重要区别的。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活动不以健康以外的竞争为目的,不去追求某种超乎常态的体能和叹为观止的对抗,因而便不会导致身体机能的片面发展,也不会带来某些不必要的危险和牺牲。然而,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活动既不构成人对自然的挑战,也不构成人与人的抗衡,因而既弱化了竞争的机制,也弱化了冒险的热情。现在大家都在探讨中国足球上不去的原因,然而在我看来,这一原因不能仅从体能、经验和制度层面去寻找,还应在更深的民族心理层面上去探求:看看我们的内心深处是否缺少着一种使足球成其为足球的狄俄尼索斯式的感性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