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走过的路
-
2 我走过的路
我求学所走过的路是很曲折的。现在让我从童年的记忆开始,一直讲到读完研究院为止,即从1937到1962年。这是我的学生时代的全部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37—1946,乡村的生活;1946—1955,大动乱中的流浪;1955—1962,美国学院中的进修。
我变成了一个乡下孩子
我是1930年在中国天津出生的,从出生到1937年冬天,我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但是时间都很短,记忆也很零碎。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开始,我的生活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矗这一年的初冬,大概是10月左右,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的官庄乡。这是我童年记阮的开始,今天回想起来,好像还是昨天的事一样。
 让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故乡——潜山县官庄乡。这是一个离安庆不远的乡村,今天乘公共汽车只用四小时便可到达,但那时安庆和官庄之间还没有公路,步行要走三天。官庄是在群山环抱之中,既贫穷又闭塞,和外面的现代世界是完全隔离的。官庄没有任何现的设备,如电灯、自来水、汽车,人民过的仍然是原始的农村生活。对于幼年的我,这个变化太大也太快了,在短短的三天之内我顿然从一个都市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乡下的孩子。也就从这时开始,我的记忆变得完整了,清楚了。乡居的记忆从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首先我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我的住屋前面有一道清溪,那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后和左、右都是山岗,长满了松和杉,夏天绿阴密布,日光从落叶中透射过来,暑气全消。我从七八岁到十三四岁时,曾在河边和山上度过无数的下午和黄昏。有时候躺在浓绿覆罩下的后山草地之上,听鸟语蝉鸣,浑然忘我,和天地万物打成了一片。这大概便是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一种境界吧!这可以说是我童年所受的自然教育。
让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故乡——潜山县官庄乡。这是一个离安庆不远的乡村,今天乘公共汽车只用四小时便可到达,但那时安庆和官庄之间还没有公路,步行要走三天。官庄是在群山环抱之中,既贫穷又闭塞,和外面的现代世界是完全隔离的。官庄没有任何现的设备,如电灯、自来水、汽车,人民过的仍然是原始的农村生活。对于幼年的我,这个变化太大也太快了,在短短的三天之内我顿然从一个都市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乡下的孩子。也就从这时开始,我的记忆变得完整了,清楚了。乡居的记忆从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首先我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我的住屋前面有一道清溪,那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后和左、右都是山岗,长满了松和杉,夏天绿阴密布,日光从落叶中透射过来,暑气全消。我从七八岁到十三四岁时,曾在河边和山上度过无数的下午和黄昏。有时候躺在浓绿覆罩下的后山草地之上,听鸟语蝉鸣,浑然忘我,和天地万物打成了一片。这大概便是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一种境界吧!这可以说是我童年所受的自然教育。
现在我要谈谈我在乡间所受的书本教育。我离开安庆城时,已开始上小学了。但我的故乡官庄根本没有现代式的学校,我的现代教育因此便中断了。在最初五六年中,我仅断断续续上过三四年的“私塾”;这是纯传统式的教学,由一位教师带领着十几个年岁不同的学生读书。因为学生的程度不同,所读的书也不同。年纪大的可以读《四书》、《五经》之类,年纪小而刚刚启蒙的则读《三字经》、《百家姓》,我开始是属于“启蒙”的一组,但后来得到老师的许可,也旁听一些历史故事的讲解,包括《左传》、《战国策》等。总之,我早年的教育只限于中国古书,一切现代课程都没有接触过。但真正引起我读书兴趣的不是经、史、古文而是小说。大概在十岁以前,我偶在家中找到了一部残破的《罗通扫北》的历史演义,读得津津有味,虽然小说中有许多字都不认识,但读下去便慢匣猜出了字的意义。从此发展下去,我读遍了乡间能找得到的古典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荡寇志》(这是反《水浒传》的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我相信小说对我的帮助比经、史、古文还要大,使我终于能掌握了中国文字的规则。
大动乱中的流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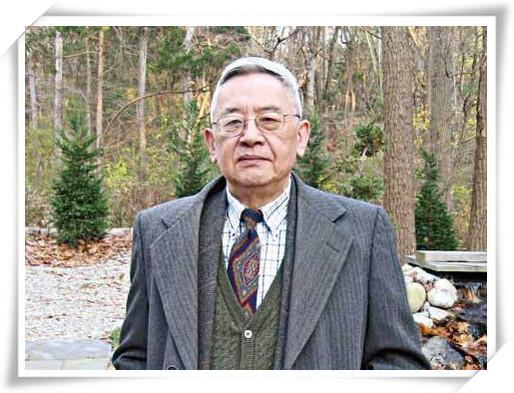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正在桐城。因为等待着父亲接我到外面的大城市去读书,便在桐城的亲戚家中间住着,没有上学。第二年(1946)的夏天,我才和分别了九年的父亲会面。这里要补说一句:父亲在战争时期一直在重庆,我是跟着伯父一家回到乡间逃避战乱的。我的父亲是历史学家,学的是西洋史,战前在各大学任教授,1945年他去了沈阳,创立了一所新的大学——东北中正大学。i946年6月我先到南京,再经过北平,然后去了沈阳。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正在桐城。因为等待着父亲接我到外面的大城市去读书,便在桐城的亲戚家中间住着,没有上学。第二年(1946)的夏天,我才和分别了九年的父亲会面。这里要补说一句:父亲在战争时期一直在重庆,我是跟着伯父一家回到乡间逃避战乱的。我的父亲是历史学家,学的是西洋史,战前在各大学任教授,1945年他去了沈阳,创立了一所新的大学——东北中正大学。i946年6月我先到南京,再经过北平,然后去了沈阳。
这时我已十六岁了,父亲急着要我在最短时间内补修各种现代课程,准备考进大学。1946--1947这一年,我一方面在高中读书,一方面在课外加紧跟不同的老师补习,主要是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目。我在这一年中,日夜赶修这些课程,希望一年以后可以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一篇短短的英文文字,其中便有八十多个字汇是陌生的。这时我已清楚地认识到,我大概决不可能专修自然科学了,我只能向人文科学方面去发展。好在我的兴趣已完全倾向于历史和哲学,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1947年夏天,我居然考取了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我的治学道路也就此决定了。
我本来是不准备离开中国大陆的。但1949年年底,我意外地收到母亲从香港来信,原来他们又从台北移居到香港。1950年元月初,我到香港探望父母,终于留了下来,从此成为一个海外的“流亡者”。一个月后,我进入新亚书院,这是我的大学生活中所走的最后一段路。
新亚书院是一所流亡者的学校,由著名的史学家钱穆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1949年秋天创办的,学生人数不多,也都是从大陆流亡到香港的。从此我变成钱先生的弟子,奠定了我以后的学术基础。
美国的进修
 我在新亚时代,在钱先生指导之下,比较切实地研读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原始典籍。与此同时,我又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协会两个图书馆中借阅西方史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新书。但我在香港时对西方学问仍是在暗中摸索,理解是肤浅的。1955年到哈佛大学以后,我才有机会修课和有系统地读西方书籍。我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在这一方面我至少已有了一段的基础。在哈佛大学的最初两三年,我比较集中精力读西方的史学和思想史。所以我正式研修的课程包括罗马史、西方古代与中古政治思想史、历史哲学、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我并不妄想在西方学问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识,以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参考资料。
我在新亚时代,在钱先生指导之下,比较切实地研读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原始典籍。与此同时,我又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协会两个图书馆中借阅西方史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新书。但我在香港时对西方学问仍是在暗中摸索,理解是肤浅的。1955年到哈佛大学以后,我才有机会修课和有系统地读西方书籍。我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在这一方面我至少已有了一段的基础。在哈佛大学的最初两三年,我比较集中精力读西方的史学和思想史。所以我正式研修的课程包括罗马史、西方古代与中古政治思想史、历史哲学、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我并不妄想在西方学问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识,以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参考资料。
由于我从童年到大学时代都在战争和流亡中度过,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按部就班的知识训练,我对于在美国研究院进修的机会是十分珍惜的。从1955年秋季到1962年1月,我一共有六年半的时间在哈佛大学安心地读书。第一年我是“访问学人”,以后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接受严格的学术纪律的阶段。这一段训练纠正了我以往十八年(1937—1955)的自由散漫、随兴所之的读书作风。依我前十八年的作风,我纵然能博览群书,最后终免不了泛滥无归的大毛病,在知识上是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创获的。尽管我今天仍然所知甚少,但我至少真正认识到学问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的运气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钱先生,在哈佛大学又得到杨联隍教授的指导。杨先生特别富于批评的能力,又以考证谨严著称于世。他和钱先生的气魄宏大和擅长综合不同,他的特色是眼光锐利、分析精到和评论深刻。这是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学者典型。杨先生和日本汉学界的关系最深,吉川幸次郎和宫崎市定都是他的好朋友。在杨先生的鼓励之下,我也对日本汉学界的发展一直在注意之中。这又是我在哈佛大学所获得的另一教益,至今不敢或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