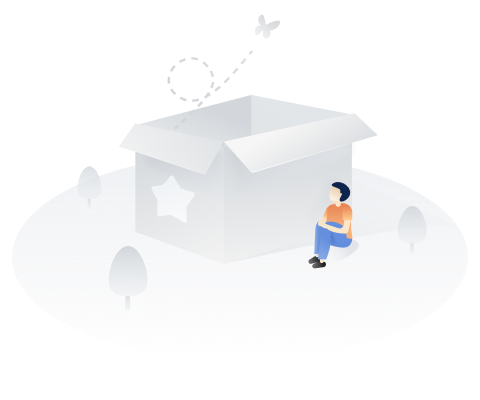-
1 为儒学的21世纪前...
-
2 为儒学的21世纪前...
-
3
一、 对“新教伦理”的诠释
在余英时看来,韦伯的理论贡献在于:指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与精神的原因,这样的一种原因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背景,这也就是所谓的“新教伦理”,也称为入世苦行。
 韦伯认为,加尔文的入世苦行的思想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他的研究在地域上侧重此种思想所波及的地区如荷兰、英国等地。这一精神的基本要素被以下信仰公式所表达:勤勉——节俭——天职——罪。如余英时所表达,新教精神中包括了勤、俭、诚实、有信用等美德,但更注意鼓励人们“以钱生钱,而且人生就是以赚钱为目的,不过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换句话说,赚钱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义之所在’”。这样的精神似乎是超越非理性的,“但更奇妙的则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人必须用一切最理想的方法来实现这一‘非理性的’目的”。
韦伯认为,加尔文的入世苦行的思想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他的研究在地域上侧重此种思想所波及的地区如荷兰、英国等地。这一精神的基本要素被以下信仰公式所表达:勤勉——节俭——天职——罪。如余英时所表达,新教精神中包括了勤、俭、诚实、有信用等美德,但更注意鼓励人们“以钱生钱,而且人生就是以赚钱为目的,不过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换句话说,赚钱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义之所在’”。这样的精神似乎是超越非理性的,“但更奇妙的则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人必须用一切最理想的方法来实现这一‘非理性的’目的”。
他将韦伯思想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比较,指出韦伯所论,自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理论,因此不可原封不动的套用于中国史研究。但韦伯的理论又和马克思的理论一样,“其中含有新观点与新方法”,足以启发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研究。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韦伯认为文化与精神也可以在历史运行中发生重要作用。
不过韦伯也不是“历史唯心论者”,他在肯定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认为资本主义不纯粹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如余英时所分析,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归结于三个互相独立的历史因素: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思想。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是在此三者交互影响下发生的。这样,韦伯便从多元视野,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起因与结果,作出广泛意义上的判断。他对新教伦理与西方发展的关系所做的不同凡响的解读,某种意义上启发历史学家对世界社会发展史做重新审订。
二、一个“韦伯式的问题”
余英时论及唐代佛教变化,指论从社会史角度来看,重要一点就是从出世转向入世。而惠能所创造的新禅宗,在这一发展上尤具突破性和革命性的成就。余英时说,有人称们是中国的马丁·路德是有理由的。惠能立教的基本意义是“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后世通行的《坛经·机缘品》记录他的话,有“字即不识,即请问”等语。他还说,惠能有“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之说,在当时佛教界是一个狮子吼。 佛教精神从出世转向入世,便是从这一句话中体现出来。不过余英时也承认,惠能的宗教革命最初仅限于佛教范围之内,而且唐代的宗教派别甚多,禅宗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这一革命实际上是静悄悄地发生在宗教世界的一个角落里,并没有掀动整个 世俗的社会。
世俗的社会。
余英时在说到新道教时,称道全真教云:全真教有两个理论,一是“默谈玄机”,即是“识性见性为宗”;一是“打劳尘”,即是“损己利物为行”。所要说的是若无前者,终生在劳动中打滚,永无超越的可能;若无后者,则空守一心,也不能成道。余英时说,这实际上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稍知加尔文教义者不难看出这正符合‘以实际意识和冷静的功利观念与出世目的相结合。’”余英时论全真教与禅宗也有不同的地方,它的入世倾向在一开始便比较明显,比禅宗来得更直接与深切。新道教对中国民间有深而广的影响,其中有一个思想,便是天上的神仙往往要下凡历劫,在人间完成“事业”以后才能“成正果”、“归仙位”。同时凡人要是想成仙也必须“做善事”、“立功行”。
余英时说,新儒家将浪费时间看作是最大的罪恶,与新教伦理毫无二致。不过他说,“在这一问题上新儒家其实也受到了佛教的刺激”。朱熹有言,“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些子事,无道理。” 余英时解释云:这里所说的做事虽然不全部说是生产劳动,但其所宣扬的是只要在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则可以心中无愧。这和新教的工作观依然十分相似。新教认为人必须有“常业”。不是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同一类职业,即使不是体力劳动,只要为上帝努力“做事”即可。余英时说,只要将上帝换为“天理”,即可发现新儒家的社会伦理有许多与新儒家的思想合节。 新儒家与以往的儒教最大不同之处是前者找到了生命超越的根据。新教徒以为入世苦行是上帝的绝对命令,上帝的选民必须以此世的成就来保证彼岸的永生,新儒家则相信“天理”,人生在世,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勉“做事”以“尽本分”。做事不是消极的,必须“主敬”。主敬的方向一方面是对“事”,另一方面对于消除内心紧张来说,又其所敬方向又是对“天”,对“理”,这样中国新儒家就有了宗教承当的意义提升。前面说的是禅宗与道教。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自然会想到“儒、释、道”。余英时在论说中国传统中的近代性转化时也将目光注意到儒家。他承认中国儒学发展到明时代是一大转折,从这时候起中国儒家出现了近代性演化。
三、心、性说新解与“信仰得救”
中国禅宗强调“心、性”。《坛经》第二十八节说“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知慧观照,不假字。”余英时解说惠能的观点与马丁·路德的思想已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即重在“本性”,自由解经,“不死在句下”。敦煌写本《坛经》三十一节说:“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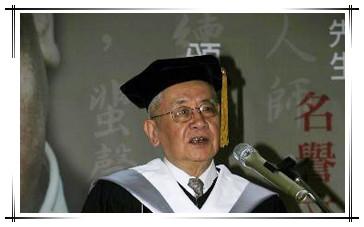 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得善知识示道见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识。若求善知识,望得解脱,无有是处。识自心内善知识,即得脱。”
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得善知识示道见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识。若求善知识,望得解脱,无有是处。识自心内善知识,即得脱。”
余英时说,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事实,即新禅宗对新儒家的最大影响不在“此岸”而在“彼岸”。儒家自始即在“此岸”,是所谓“世教”,在这一方面自无待于佛教的启示。但是到了南北朝之后,佛教与儒学士大夫都已经看到儒家只有“此岸”而无“彼岸”,以儒家的习用语言即是有“用”而无“体”、有“事”而无“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新儒家因新禅宗的挑战而开展自己的心性论,最后找到了“彼岸”。但是也要看到新儒家的“彼岸”论一开始就不同于佛教的彼岸论,儒家的彼岸是“实有”而不是“空寂”。诚如朱子所说:“儒释言性异处只是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 所以儒家所建立的“彼岸”只能是“理”的世界与形而上的世界。同时中国心性论的建立又表明,一个信仰者只有通过对“心”的关照,才能获得对“理”的觉悟。
四、忧心
 余英时也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恐其将为“游魂”。
余英时也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恐其将为“游魂”。
他说,从全面来看,中国近世的宗教转向其最初发动之地是新禅宗。
新儒家的运动是第二波;新道教更迟,是第三波。这是唐宋以来中国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 . 然而儒家于中国将来的命运究竟是怎样的呢?中国有没有儒家复兴的希望?中国以至东亚是不是如同杜维明所说的有一个“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对于以上的问题,余英时的论文透出些须的疑惑,为儒家于今后的困境为难。
关于儒学再兴,余英时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是致力发挥其固有的“践履”精神与“人伦日用”性格,还是象现在这样仅将其局限于一种“论说”。如属前者,儒学便以“游魂”为其现代命运。后者,“则怎样在儒家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联系”,又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