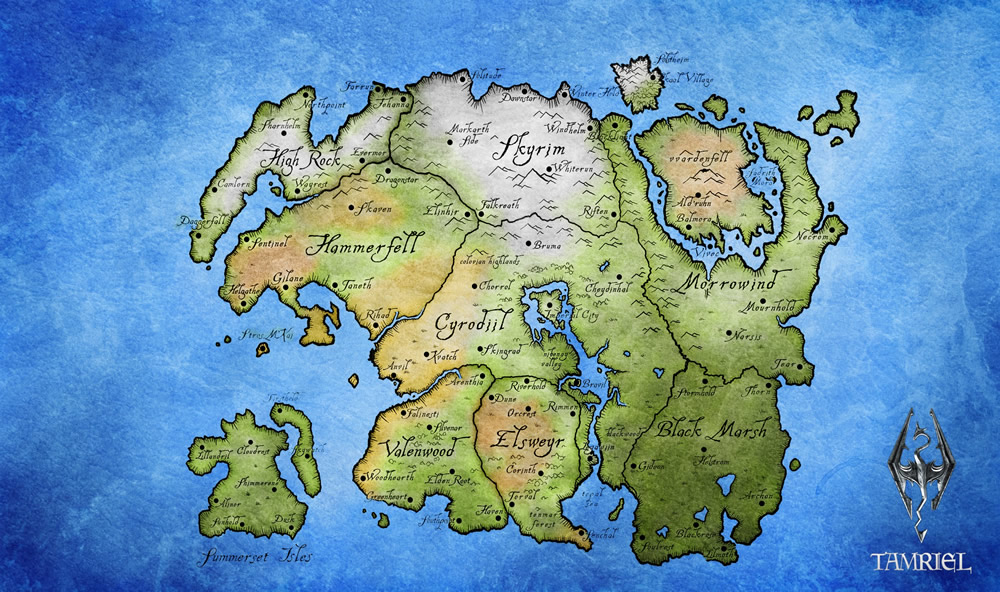全球化与美国宗教改革
从公民宗教的角度看,人民主权为美国人的政治生活提供了终极意义,公民权就成为美国人参与人民主权的法律途径,美国宪政的历史可以看作是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史。美国法学家卡汉认为,人们不能仅仅在正义、自由这些理性主义的话语中来谈论主权,民族国家中的积极主权从来都是一种情感现象,在美国至今如此。

二战之后,随着对法西斯主义及其背后民族主义的反思,尤其欧盟作为超民族国家的制度建构逐步获得了成功,欧洲彻底完成了对附着于民族国家概念上的宗教色彩的祛魅工作,从而将欧洲国家或欧盟完全奠基于“人权”这个世俗化的概念基础上。因此,后冷战时期的欧盟积极回应安南关于反思国家主权的呼吁,主张在全球化时代应当抛弃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在人权基础上重新奠定国际新秩序,从而把后冷战时期的美国超级霸权批评为“新罗马帝国”。而美国则不断宣扬“美国例外论”,坚持国家主权至上,不受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约束。这种分歧不仅是美国与欧盟的政治利益的分歧,更有深刻的思想分歧。按照卡汉的观点,安南和欧盟在主权问题上对美国发出的呼吁不亚于一场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的核心在于争夺信仰解释权,清教徒主张信仰不是通过参与教会规定的仪式来体现,而是通过对圣经文本来理解上帝的意旨。清教徒的上帝由此变成了一个话语的世界,可以有分歧,可以进行解释,可以进行辩论。
宗教改革无疑剥夺了教会和教士的权威,也推动了多元主义政治观念的发展。自由市场、人权保护和民主政治都得益于宗教改革。在政教分离原则之下,国家主权依然保持了自己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宗教改革带来的多元主义首先体现在民族国家之间,而民族国家本身却从教会中获得了普遍的灵感,国家主权反对分裂、分离和分割。积极主权就是一种参与神圣的体验。因此,人民主权的神依然是地方性的神。在宗教改革背景下,人民主权抛弃了君主,而与有机的人民联系在一起。人民主权的任务就是通过深思熟虑和自我选择之后形成“主权人民”。一方面人民往往通过革命这个构成性的行动而形成,另一方面人民也通过自己的言语(宪法)而构成。可以说,民族国家和人民主权既保留了基督教的传统,又吸收了宗教改革的成果。“现代人民主权政治的成就就在于将教会的有机统一与启蒙时代对理性的信仰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结合在美国就形成了人民主权与宪法(法治)统一,由此形成了“自由主义的国家教会”(nationalchurchofliberalism)。
对美国而言,后冷战时期对国家主权的攻击就类似于当年清教徒对教会的攻击。美国这个国家是通过牺牲这样的宗教信念凝聚起来的,国家类似于教会,是公民获得生存意义的地方。但安南和欧盟所主张的“个体主权”背后所隐含的“国家工具论”中,国家的目的通过测量总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疾病率来表达的。工作取代了牺牲,生产体系取代了牺牲体系。政治不再是目的,而变成了手段。全球化时代就是一个个体主义的时代,这不是因为个体那里有什么实质性的真理,而是由于全球化促使启蒙思想与产生清教主义的基督教信仰进一步相互交叉。意义变成了一种个体的信仰,由个体来选择加入哪一个解释的共同体。
在人权概念的基础上,全球化者认为美国例外论不过是美国虚伪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主权论者则把全球化者看作是美国的潜在敌人,正试图用全球体制来瓦解美国的权力,并试图在美国推动一场宗教改革运动,要求美国放弃人民主权背后的基督教神学的意含,将国家主权完全奠基于世俗化的人权概念基础上。这种意识形态争论的背后,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必须按照真理生活,还是真理不过是话语的对象?”换句话说,政治完全是理性的,还是涉及到神圣的信仰问题;信仰究竟是个体的,还是必须在一个共同体中获得意义?这是美国与欧盟之间没有终结的辩论。